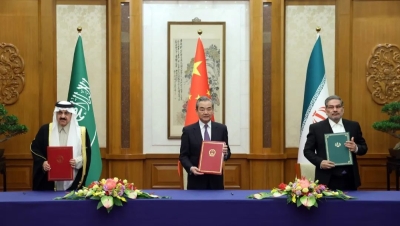【來論】劉兆佳:“自由國際秩序”的坍塌不應歸咎中國近年來美國不斷無端指責中國蓄意破壞和挑戰國際秩序。恰恰相反,美國應該對其所建構和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坍塌負主要責任,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使這個秩序難以維繼,並窒礙其他國家發展,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重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新國際秩序成為國際社會的強烈呼聲。 近年來,為了遏制和孤立中國,美國屢次指控中國不斷漠視、濫用、扭曲、破壞或違反美國主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制度和規則。美國宣稱中國行動的最終目的不單是要徹底摧毀這個國際秩序,更是要在其廢墟上建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體現“威權主義”和服務中國利益、以中國的主觀喜好取代現有制度和規則的“非自由國際秩序”。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其2022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中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重塑國際秩序,也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達到這個目標的競爭者”。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2022年在華盛頓的亞洲協會發言時表示,儘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華盛 頓將繼續瞄準中國,將其視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最嚴重威脅。布林肯說,中國是唯一有意願和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而且它這樣做的方法必然會破壞全球穩定,“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在過去75年讓世界得以取得多方面進步的普世價值觀”。 美國建立並主導的國際秩序早已問題叢生 事實上,遠在美國指控中國破壞國際秩序之前,美國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已經出現崩壞不斷和無以為繼的跡象。因此,把中國當作這個國際秩序坍塌的罪魁禍首並不公平和合理,也明顯懷有遏制中國的意圖。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罕有地承認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過去幾十年出現了裂痕。也即是說,那個“自由國際秩序”在中國“ 蓄意”對其“破壞”之前已經問題叢生。 時至今天,這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但在衆多發展中國家中失去認受性,就連西方國家內部質疑的聲音也此起彼落,而且越來越響亮。印度學者兼前外交官員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shankar Menon)明言,“沒有人想要當前的世界秩序,而似乎只有越來越少的國家,包括那些建立了先前國際秩序的國家,仍致力於維護它。”南非學者蒂姆·穆里蒂(Tim Murithi)直指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一種“壓迫秩序”(Order of Suppression),從來都不符合非洲的利益。美國學者菲利普·澤利科夫(Philip Zelikow)更形容這個國際秩序為“空心秩序”(the Hollow Order),原因是在過去十年中,管理全球資本主義的機構已經淪為比實質更重要的作秀。他特別提到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等國際機構已經受到美國的干擾和抵制而難以正常運作。 那個“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走向式微,主要原因是這個秩序本身的內在缺陷不斷暴露和惡化,以及美國自己又對它缺乏尊重並逐漸背離,所以絕對不是所謂“中國惡意破壞”所致。 這個二戰後誕生的“自由國際秩序”從設計到運作都是由美國主導,其核心目的是維護和強化美國乃至西方的國家利益和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元霸權,因此從一開始便不是一個公平、平等和包容的國際秩序。這個國際秩序的遊戲規則依據美國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而設計,讓美國和其領導的西方集團享有大量特權,從而把它們置於絕對有利的位置上,而對其他國家的發展和自主則形成了强大的制約。美國主導建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其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美元作為首要的國際貨幣,美國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多邊主義等,都是那個“自由國際秩序”的支柱。剛去世的台灣學者朱雲漢曾指出:“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貿易規則,往往蘊含了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間的不平等交換與支配宰制關係。”穆里蒂認為,這個秩序“保持了世界主要大國 [……] 維持其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主導地位的現狀。”在那個秩序下,“大國不再像過去那樣用蠻力奪取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是依靠優惠貿易協議和不正當的融資安排來耗盡非洲大陸的資源,並通常是通過勾結腐敗的非洲精英而獲得。”所以,“非洲沒有人相信國際秩序是建立在規則之上的。” “自由國際秩序”讓美西方國家獲利而窒礙他國發展 不爭的事實是,這個“自由國際秩序”的長時間運作窒礙了不少國家的發展,部分國家甚至長時間陷入貧困的深淵,也導致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和政治嫌隙不斷擴大,引起了“ 全球南方”的不滿和抗拒。即使在西方國家內部,貧富懸殊、財富集中、中產階層愈趨萎縮、勞工階層困頓、去工業化、金融危機屢發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亦比比皆是,這些情況為反全球化浪潮、保護主義、排外情緒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參與那個“自由國際秩序”之同時又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在美國的唆使和壓力下全盤接受西方的發展模式,反而逐漸開拓出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和成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而且多次對那個“自由國際秩序”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建議。對美國而言,中國的發展模式不但“離經叛道”,甚至對那個“自由國際秩序”和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嚴重挑戰,所以必須予以遏制和打擊。 那個在西方和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失去認受性的“自由國際秩序”在蘇聯解體、美國單極霸權崛起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睥睨一切後出現“範式性”的轉變(Paradigmatic Shift)。在新的“自由國際秩序”下,美國以各種手段包括政權變革(Regime Change)要求、引誘、推動或強制所有參與那個新“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都採納美國或西方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發展模式以及價值觀。實際上,這是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自主的蔑視。與此同時,美國在本國和在那個新“自由國際秩序”中最大化地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金融和貿易全球化、商品和人員自由流動、經濟活動管制的撤銷,以及政府的經濟、社會和福利功能的壓縮、公共開支削減、大幅減稅,從而讓美國的跨國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能夠暢通無阻地在其他國家掠奪它們的財富。新自由主義的狂飆的確讓美國的金融和貿易巨頭獲利甚豐,但同時也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頻密爆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鴻溝不斷擴大、各國的債務愈趨沉重、氣候變化危機加劇和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惡化等棘手難題。 無可避免地,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新國際秩序比之前的舊“自由國際秩序”更難以為發展中國家所接受。梅農講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領導了兩種秩序:一種是凱恩斯秩序(the Keynesian Order),它對兩極冷戰世界中各國如何處理其內部事務不太感興趣 [……] 。第二種是那個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中出現的、漠視其他國家賴以維護其利益的主權和邊界的新自由主義秩序。這兩個秩序都宣稱是『開放的、基於規則的和自由的』,以及是那些所謂自由市場、人權和法治的民主價值觀的捍衛者。實際上,它們依賴美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的主導和必要地位。” 賴恩·穆勒森(Rein Mullerson)認為,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新“自由國際秩序”其實並不那麽自由。“相反,這是一種自由國家統治世界的秩序,它們試圖擴大自由社會的範圍(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同時排斥甚至摧毀那些不能或不想變成 [西方式] 自由社會的國家。” 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ar)指出,由於新自由主義作祟,美國作為單極世界中的霸主不願意接受一個多樣化的世界,這遂使得其所主導的新“自由國際秩序”更加失去國際認受性。他告誡說:“如果華盛頓希望維持一個有助於避免衝突、促進繁榮和促進自由價值觀的國際體系,它就必須擁抱一種更加多樣化的秩序——一種能夠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針對不同問題用不同方式運作的秩序。”就連一貫謳歌“自由國際秩序”的美國學者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認為要維繫這個新秩序,這個新秩序的“成員的資格不應該取決於它們的政權的性質,而應該僅取決於對它們國家主權地位的承認和它們履行成員責任的承諾和能力。”也就是說,奉行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應該成為新的國際秩序的成員,而“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和“反對霸權”則應該是建構這個新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可惜的是,美國根本不願意尊重各國選擇自己的制度、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因此難以得到衆多非西方成員對新“自由國際秩序”的認同和歸心,而美國這種“唯我獨尊”的心態同時也妨礙了一個由世界各國共同建構的公平和合理的新國際秩序的出現。 “自由國際秩序”遭到美西方國家內部批評 新自由主義的冒起,在美國和大部分西方國家也激化了嚴重內部矛盾,導致西方民衆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反感不斷上升。在此之前,舊“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在西方社會得到相當程度的接受,是因為在不斷推動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同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和資產階級與西方群衆特別是中產和工人階級訂立了一張保障他們基本利益和福祉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以彌補他們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下所蒙受的衝擊和損害。可是,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坍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資產階級覺得不再有需要與其他階級進行“階級妥協”。以美國為例,加里格·斯特爾(Gary Gerstle)指出:“勞資之間的妥協是 [羅斯福總統]『新政』New Deal)秩序的基礎。工人獲得了累進稅、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工會組織權、國家對充分就業的承諾、政府對集體談判的支持以及對貧富不平等的限制。[……] 在20世紀90年代,資本仍然需要美國政府的幫助來規範市場。共產主義一直是資本最難纏的對手,但在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裡,它覺得與勞工妥協的必要性越來越少。”結果是,美國過去給中產和勞工階級的保障和福利大幅減少,並漠視對他們在全球化下蒙受的衝擊,從而激發了他們對新“自由國際秩序”的不滿和反彈,催生了西方世界內部反全球化、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滔天巨浪。 事實上,即便美國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制定者和首要獲益者,但它經常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尊重和違反自己建構的制度和規則。威廉·德羅茲迪亞克(William Drozdiak)指出,由於忽視、管理不善和美國給予支持的減少,那些美國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支柱,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正在搖搖欲墜。美國對這些關鍵機構表現出的漠視削弱了它們的權力和影響力。很多時候,美國以單方面的方式行事,只是選擇性地尊重它曾經誓言要維護的國際秩序規則。 近年來,由於美國民衆和部分政治精英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認同和支持持續下滑,這類事情發生的頻率不斷上升,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大纛下更是變本加厲,他在任時開展對各國特別對中國的貿易戰、對國際組織和規則的蔑視,這些是美國逐漸背離其建構“自由國際秩序”承諾的證據。現任總統拜登在相當程度上其實延續了特朗普的方針。2023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發言,充分表明了美國今後脫離新“自由國際秩序”的意圖。他強烈譴責對新自由主義尤其是對自由市場的篤信給美國帶來的禍害,包括金融業的過度膨脹、現代製造業的萎縮和中產階層的沒落。因此,美國必須推行現代工業和創新策略。在新的工業政策下,美國會物色和扶持一些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對國家安全有戰略意義、而私營企業還沒有準備好投資的產業,從而讓美國的雄心壯志得到實現。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斷言,過去支撐“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已經不再。新的“華盛頓共識”是以維護美國利益為鵠的的“教義”。他認為:“新的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華盛頓本身,而不是在冷戰結束後設定全球標準的狂妄自大的美國。”“它確實有經濟工具,例如回流供應鏈、優先考慮彈性而不是效率,以及產業政策。但這些主要是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今天的美國無法達成貿易協議,無法談判全球數字規則,無法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無法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改革。華盛頓對經濟多邊主義失去了信心。”美國不再願意履行其對國際秩序的責任和承擔,是國際秩序“空心化”的主因。正如澤利科所言:“由於國內反對,美國無法加入新的貿易協定。全球各國債務堆積如山,當前的國際經濟體系無法協調如何減少債務或提供必要的救濟。世界貿易組織的運作即將停止,一方面是因為它無法使其規則現代化,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拒絕確認仲裁者,故意使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癱瘓。但當前世界秩序的空洞性在全球衞生領域最為明顯。” 總而言之,美國應該對其所建構和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坍塌負上主要責任,而不應該責怪中國。相反,美國應該放棄其霸權主義並尋求與中國平等相待、和平共處和互利共贏之道,並與中國和其他國家一起合力結束當前國際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的局面,重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充分照顧各國特殊情況、讓所有成員都能獲益和能夠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新國際秩序。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崔靜雯】
|